
旅以载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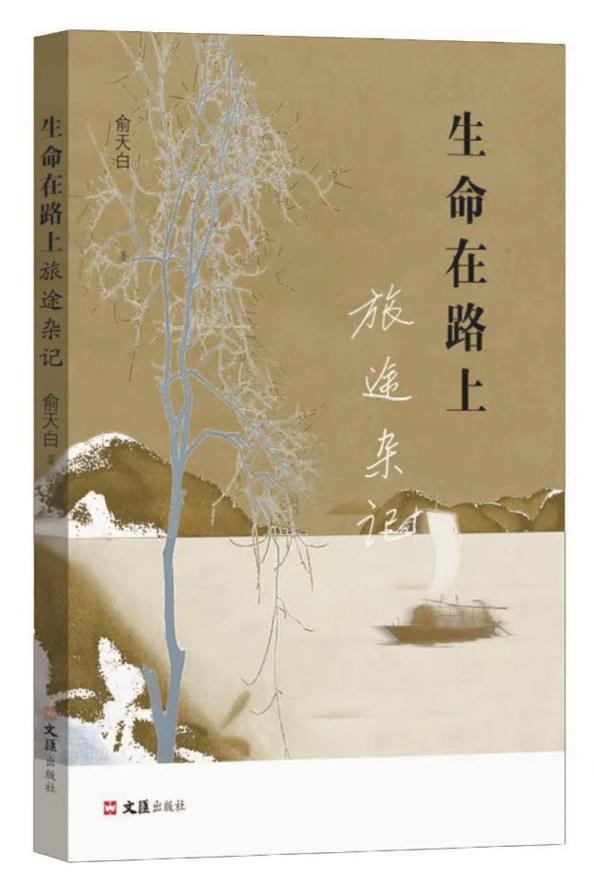
◆俞可
让我们“在读”中悦读 悦心 悦人
俞可:上海师范大学中德教育研究与协作中心总干事
游记虽非小说家的创作主体,但展现的是与自然、社会、内心的对话,迸射的更是生命之张力与美学。自2016年1月22日,俞天白在《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开启个人专栏《行走“天地之中”》。母本是其历年行旅所撰日记,取名《生命在路上——旅途杂记》(简称《旅途杂记》),近日由文汇出版社推出。
以《江山易改,不废韩江万古流》为压轴篇章,俞天白致敬韩愈。因《古文观止》自幼烂熟于心,游潮州,临韩江,俞天白叹道:“水光山色,古刹名都,只要参见过这样的江河,就不虚此行了!”苏轼盛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敬奉的乃“修其辞以明其道”(韩愈《争臣论》),即文以载道。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根基在道:行其旅以明其道,由以旅化人而以文化人。旅以载道,《旅途杂记》在三个层面铺展所载之道:天道、世道、人道。
就主题而言,《旅途杂记》描绘的是山川,以行作工具,载以天道。收录《旅途杂记》的皆为作者参加作家笔会、编辑组稿、记者采访、文化研讨等文学生活。“自幼景仰的严子陵先生及其钓台,总算亲临其境了,不能不算是人生快事。……幼时读《石钟山记》,写的就是这里!……酒泉、武威,都属河西走廊重镇,那些脍炙人口的边塞诗中出现的地名,幼时就印入了我的心中,无不以到此为快。”告别学舍,走出书斋,古典诗词中诵读的意象山水得以具象化,应目会心,物我一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董其昌《画旨》)。
以天授之气韵,《旅途杂记》回放的实为作者以一生完成的一场文学壮游。故不录者有二:度假与出访。度假无关乎文学,出访则无涉于祖国。“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王国维《人间词话》)。诗言志、诗缘情,且皆萌发于自然。缘山水之情,言山河之志。山水转化为山河,维系于赤子之心。从头至尾走完长城,“正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整整一个甲子,在一个不经意间,以如此完美的方式,理解了作为华夏之子所存在的环境,以及如何才能体现生命的价值。这不是上苍刻意帮我确定‘生命在路上’的原理,还能做什么解释?”家国情怀溢于山水之间,赤子心中的山河冉冉升起。
就体裁而言,《旅途杂记》采用的是日记,以录作工具,载以世道。日记是一种记录社会、反思生活、观照自我的书写样态,属非虚构文体,价值在于史料性。早年意大利之行所存日记,直至晚年,念及撰写自传,歌德方才整理出版,遂诞生四十万言《意大利游记》。史料性价值首先体现于自传。日记的魅力则在于私密性。
旅途中的俞天白,最忠实的伴侣就是日记本。凡所游履、感怀、倾诉,皆录之于册,如重释瘦西湖之“瘦”,以生态美学揭示世间万物相依互存。
阿英1933年6月化名阮无名选编的《日记文学丛选(语体卷)》(上海南强书局)分四卷出版:记游日记、社会考察日记、私生活日记、读书日记。记游日记的生产置于山水的公共性与日记的私密性之张力下。
俞天白“关注的,始终是‘风物’而非景物”。怀揣千古文心行走于天地之间,耳目所及,只要有感生情,皆可成景。《旅途杂记》描述的1985年芜湖笔会赞助商“傻子瓜子”的老板年氏父子,便把改革开放初期民营企业的世态作为风物,在淋漓尽致的展现中塑造一道景物。记游者由此从景物的记录者升格为景物的创造者。“万趣融其神思”(宗炳《画山水序》)。通过景物的想象性生产,从生态到世态,作者回归心灵私语之真。
就立意而言,《旅途杂记》确立的是生命,以思作工具,载以人道。临山川,笔飞扬;望天地,思浩荡。有别于徐霞客,杖策云游,“欲尽绘天下名山胜水为通志”。以文学为镜头,《旅途杂记》聚焦的是景物,遥望则为生命的时空,把奇山异川化作生命的驿站,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以走遍长城来“纪念我的‘花甲’之行,十全十美了”,但“人生所有的完美,都是相对的、动态的,受时空制约的”。唯“领悟这一点,才算是真完美”。成为景物的,并非长城,而是人生。“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作者在《题记》末引用苏轼的禅诗,以化庸常的人生为别样的景致。此乃行旅之真谛。正如歌德从罗马致信其母:“我将变成一个新人归来……这是我的第二个生日,踏入罗马那天起,就意味着真正的再生。”好一个“再生”,一语道破行旅之生命性。鉴于日记的录与思,由捕捉山水之神而穷尽生命之道,因“澄怀味象”而“澄怀观道”(宗炳《画山水序》),每次行旅不再是一场精神流浪,而是一次灵魂升华。故而,歌德虽身居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公国文化部部长高位,却精准定义意大利之行为Bildungsreise,即新时代倡导的研学。研学即生命的成长。
出版《旅途杂记》,适逢俞天白米寿。效仿宗炳,不必哀叹“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手持该书,“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无他,“畅神而已”。当然,恰如歌德1787年2月15日罗马日记:“写作,虽归属精神,却是致远之举。”循着韩愈“气盛言宜”(《答李翊书》)之逻辑,心存道,方“气盛”,进而“行宜”且“言宜”。这是《旅途杂记》之要义,以此引导读者赴远方。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