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器官协调员的1000多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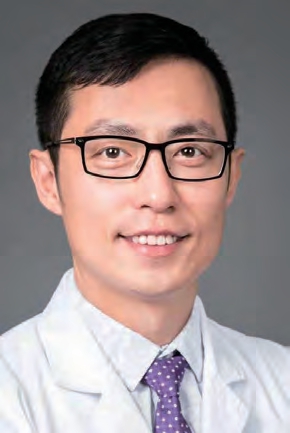
左图:高晓刚医生。

上图:高晓刚与患者在病房。

上图:器官到达医院后,马不停蹄送至手术室立刻进行移植手术。

左图:高晓刚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做人体器官捐献演讲。
记者|吴 雪
人这一生,应该看得远一点,就像电影《寻梦环游记》里一样,人的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所谓风雅,随造化、友四时也。所见无处不花,所思无处无月。花之心应为我心。
——日本俳句家松尾芭蕉在写这首俳句时,一定不会想到,有一天它会出现在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门急诊三楼的一面白墙上。
这里是一处隐蔽的区域。乍看,这面墙很普通,挂了三幅黑白素描的海报;细看,海报的笔触细腻,描绘的意境颇有故事——一束束细枝的、粗壮的、五朵花瓣的植物与花,在心脏的“土壤”中向上生长,左上角写着两个大字“器观”。
这张名为“器观”的公益海报,倡导的事情与器官捐献有关。
2015年,国家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的合法来源。经过十年推进,中国器官实现了器官来源转型——截至2021年4月,我国公民器官捐献登记人数为7万人次,每年实现器官移植手术约1万例。
前不久的一天,高晓刚穿着白大褂,从长海医院的住院区健步走来。他戴着黑框眼镜、个子高挑,是典型的医生样貌。高医生热情招呼记者到一间办公室,转身端进来一桶泡面,急促地吃上几口,说:“不好意思,还没顾上吃饭。”
高晓刚是名医生,工作状态时常如此,没点、不规律、顾不上吃饭。更特殊的是,曾经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人还没去世,他就要去谈器官捐献。
延续生命的黄金时间:72小时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是个2015年后才出现的新兴职业。
2015年前,中国拯救终末期病人的手段,通常是使用死囚犯的器官进行移植——当时没有公民自愿捐献的体系,此举实属无奈,长期下来,反而形成了负担和累赘。
此外,司法改革之后,器官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据统计,中国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每年大概有150万人,可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做上手术。
如何摆脱对死囚器官的依赖,解决这个困境呢?
最好的办法是鼓励公民自愿捐献——倡导公民在生命不可挽救时,“自愿、无偿”捐献能用的器官,让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
但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太难了。
试想一下,当一个人早上还在和家人讨论晚上买什么菜,假期去哪里玩时,突然家人就脑溢血倒地,再也救不过来的时候,有个人突然出面劝说:“把器官捐了吧。”任谁情感上都难以接受。
很多人不理解:人还没去世,哪能就要谈器官捐献?!这就牵涉到器官捐献黄金时间的问题——一般捐献黄金时间是患者发病后的72小时内:第一个24小时是家属了解病情,接受现状,通常不适合谈器官捐献;第二个24小时,需要协调员在家属接受患者病情无法救治的前提下,开始接触患者家属,谈及捐献概念;第三个24小时,如果还没推进器官捐献,往往就会由于潜在捐献者病情太重,而丧失捐献机会。
再加上器官摘取的黄金时间在心脏停跳的2到5分钟之内,之后,很快进入不可逆的损伤。所以,捐献工作必须在医学上认定潜在捐献者无法救治,处于不可逆脑损伤甚至脑死亡的状态下,立即进入捐献协调。
很多人也疑惑:为什么捐献是无偿的,但使用移植物却是有偿的?这是两个概念,后者蕴含了前期的投入成本,比如保存、运输等等。
2015年,全国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组建了这支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一开始,协调员懵懂上路,无人问津,只能做些宣传工作——协调员会根据国外协会发布的文献和辅导手册进行培训,通过学习了解器官捐献的流程和理念,知道亲属心理应激的过程,把握人的情感节奏,学会向家属解释协调员工作的意义。
在中国,人体器官协调员队伍里,一般是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有些人把协调员称为“生命摆渡人”,肩上扛着很多责任。在器官捐献过程中,对协调员的要求是很高的,既要懂得心理学,掌握社会学,还要有法律、政策、福利等各方面的知识储备,协调员是纽带,也是桥梁。
但早期这个职业不被认可和理解,也是现实。高晓刚遇见过愿意捐献的家属,也碰到过反对的、先反对后同意的,这些都很正常,体现了双方建立的沟通和信任。他做协调员的过程中,也见到了无数个中国家庭的人间百态。
“冷血”生父谈条件:捐献可以,拿钱来
高晓刚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遇到过一些拿捐献谈条件的父母,不为生命的延续,而是为了钱。
2017年,有一个在崇明岛打工的小伙子,务工期间出了严重的事故,送到医院后,治愈的希望渺茫。协调员介入想要做些工作,但得知一个情况:小伙子的父母很早就分居,一直没领离婚证,小伙子一直和妈妈生活。
奇怪的是,这个时候,一直不打照面的小伙子爸爸,突然出现了,找到协调员,张口提了两点要求:第一,孩子养这么大不容易,如果要做器官捐献,能有什么经济上的补偿;第二,打听受捐献者的家庭,对方认为,既然儿子的器官移植到受者的身体里,就把移植患者当自己的孩子,逢年过节他会去移植受者家里看看“儿子”的。
协调员认为这样的诉求特别不合理。首先,器官捐献不能和经济利益挂钩,这是大忌;其次,器官捐献后,放在网上统一分配流转,所有的医生和协调员都不知晓捐者的信息。但显然,这位父亲,在谈判之前,就认真研究了器官捐献流程的关键,那就是——只要是捐献者,父母都要签字确认。作为小伙子的生父,他恰恰握着一个签字确认权。像这种讲条件、开价的情况,把捐献直接当作生意和交易,协调员会坚决予以拒绝,不会再和他接触了。
假如为了顺利获得器官捐献而答应一些无原则的事情,都会给未来埋下隐患——2018年,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人民医院的案子,在整个业内,一直是个警醒。
当时医院重症科主任等6人,在没有红十字会人员在场监督、见证,未经批准跨地区进行人体器官捐献及没有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共同签字确认器官捐献等情况下,实施尸体器官摘取手术,非法捐献获利,分别被判刑。
高晓刚表示,协调员不会做谋利的事,也不允许捐献者家属把捐献当生意来做。但是假如碰到一些弱势群体,协调员会酌情考虑,尽力提供帮助,如果力量不够,还会向省级红十字会反映情况,引导更多爱心力量来提供帮助。
例如,2020年,一位快递小哥意外车祸去世,家人同意器官捐献。当时他妻子还怀着二胎,坚持孕育这个小生命。可是等孩子出生后,却发现孩子罹患先天性唇裂。
这时候,红十字会就介入了,从募捐到启动基金,再到联系上海九院专家会诊,目前患儿已经成功完成一期修复手术。
高晓刚说,协调员一直抱有这样的理念: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哪怕他们没有进行器官捐献,协调员知道了,可以做的,也会去援手。“当你把当事人的困难收集起来,想办法解决,得到他们的认可,他们才会信任你。”
捐献老伴儿器官,被亲戚气愤指责
器官捐献事关重要的伦理问题,在我国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里,当一个人逝世后,最为讲究身体完整地入土为安,否则就是对死者的不尊重。
但也有很多家庭,从生命延续和利他主义的角度,自愿参与器官捐献,出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曾有一对老夫妻,退休后在上海安享晚年,买了房子,做了规划,但两人没有孩子。有一天,夫妇俩在外滩跑步,老爷子突然倒地不起,后脑勺直接撞到了观光平台的硬石板路上,当时就人事不省了。送医后救治的希望渺茫,老太太便主动提出器官捐献。她说,作为丁克家族,以后没人陪她了,她准备去养老院养老,但内心的希望是,老爷子的生命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延续。
那天,老太太家里来了很多人探望,外人甚至家属都特别不理解。他们认为,老太太家境好,不缺吃穿,为何要卖老伴儿的器官赚钱?话说得不中听,但老太太有自己的想法。协调员立马就跟进了。
当时是2016年,遗体和器官捐献工作体系初步建立,神经外科的教授怕惹纠纷,赶紧翻阅最新的指南一条条核对。但高晓刚觉得不该站在谈判、风控的角度,应该和家属坐在一起坦诚地聊。老太太也觉得,越早捐献,她的先生也能留存更多。
家属有质疑,协调员就要“搭桥梁”,这个桥梁就是真正站在对方角度思考,知晓他们的想法,解决他们的难题。高晓刚坦承,“我们总以为老年人思想固执,没有与时俱进,实际上,在很多案例中,我看到有很多老年人做主的”。
一位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小儿子突然脑溢血住院了,大儿子不同意器官捐献,他认为弟弟还能活得更久。这个问题的选择权就交给了老太太,老太太做事也很清晰,说问下儿媳和孙子,孙子同意了,后来是老人做主,签了字。
结果远方亲戚来了,极力反对,各种指责,拖了一个小时探视时间。等他们走了,老太太回头和高晓刚小声说:“他们说反对意见时,我不太好表态”。高晓刚很佩服这样的老者,遗憾的是,患者病情太重,说话的时候心跳停了,最终没能完成器官捐献。
意外去世的孩子们
在高晓刚所有接触的案例中,最让他揪心、痛心的是父母为即将离世的孩子,做器官捐献决定的那一刻。
孩子都是天真烂漫的天使,协调员会遇到各种原因夭折、意外离世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没有其他的诉求,没有世俗的想法,就是为了亲情和生命的延续:快一点,再快一点,让所有的器官能救人,让所有的器官活下去。
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高晓刚心里非常感动,“因为我也是孩子的父亲,特别理解父母对孩子的爱,这样的生死离别,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一生都无法治愈的伤痛。直到现在,我的脑海里都像放电影一样,有不同的画面,不同的泪点,但最终的核心就是情感”。
媒体曾经报道过,浙江7岁的小男孩东东,意外出车祸受到重创,抢救了30个小时,没能等来奇迹,父母作出了器官捐献的决定;最近,在山东泰安,意外溺水的3岁男孩浩浩(化名),捐出了1个肝脏、2个肾脏,让3位与他年纪相仿的孩子重获新生。
其实,只是看到这样的报道,就让人情绪绷不住了。
记得2017年,有一个来自重庆的小女孩子,是学校广播站的一名广播员,会画画,学习好,是父母心里的小天使,“别人家的好孩子”。谁料,肿瘤在她的颅内悄悄生长,直到有一天,女孩在学校里突然晕倒了。
平时家长对脑部检查很轻视,再加上小朋友会闹,一般不会去查头颅的情况,只有老年人有脑梗史的才会去定期查一下。当时高晓刚就觉得情况不好,因为心脏不好兴许换一个还能救活,但脑死亡是真正的死亡。
后来在器官捐献的纪念活动上,女孩妈妈朗诵了女孩写的广播稿。在场所有人,都感动哭了。
高晓刚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大学生,也属于那种优秀的“别人家的孩子”。他是班长,女朋友是团支部书记,男孩很幸运,毕业后被一家外企留用,两人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结果,在旅游结婚的时候,男孩视觉、听觉上出现了幻视、幻听。
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大碍,他老婆还开他玩笑。但回去后,情况越来越严重,到医院检查,颅内长了胶质瘤III级,父母知道后,从老家赶来,陪伴儿子在上海某家三甲医院接受了手术治疗。术后也在其他医院接受了放射治疗。
但这些措施并没能阻止病情的发展,患者父母知道孩子救不过来了,就一直在上海医院陪着他。一家人都是知识分子,很理性地和协调员谈条件,也谈到了目前面临的困难。
男孩的父母提出,希望在孩子弥留之际,能为他提供必要的医疗看护条件,即使有医疗救助政策,他们也选择用医保范围内的救治药品,不增加医疗成本。他们愿意完成器官捐献,仿佛很理性地接受这件事,每天定时定点给孩子喂药、擦身、用药。
突然有一天,男孩的爸爸找到高晓刚说:“高医生,我儿子今天不好,我感觉我儿子可能不行了。”高晓刚过去一看,真不行了,马上启动捐献程序,进行脑死亡状态的判定。签字早就签完了,整个过程都非常非常理性。但真正到了告别的那一刻,妈妈受不了了……
高晓刚很少去回忆这些案例,但当记者提问时,案例一下子涌上来太多了,告别的画面,尤其记得清楚。高晓刚说:“我是一名医生,面对病情时我要理性,但看到这些画面,作为同样是父母的我,也受不了。”
大多数时候,高晓刚会回避和孩子家长去谈。“前期我会告知他们一些政策性的东西,会协调好力量陪护他们,但真到了要张嘴的时候,我会让没有孩子的人去张嘴,年轻的协调员硬着头皮去,没有什么技巧,就是陪着哭,陪着宣泄情绪。但是当情绪宣泄完后,他们还是希望,孩子的生命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采访进行到这里,高晓刚沉默了足足三分钟……
他的拒绝是正常的,他的同意是伟大的
做协调员多年,高晓刚通常会回避“一定要谈成”这种理念。他认为和患者家属之间,必须坦诚,才能彼此信任。
“我常常和年轻的协调员讲,任何一个患者家属,他的拒绝都是正常的,他的同意是伟大的,是应该赢得尊敬与感激的。这样的工作态度才是正确的,哪怕他们现在不同意,以后可能会转变。”事实上,高晓刚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曾经有一位大姐,打电话到医院咨询遗体捐献的事情,但医院不做遗体捐献,就介绍了器官捐献的流程及团队。了解过后,大姐没有深入再谈了。但过了好久,她一个姐妹的老公,正好在这家医院抢救,人救不过来了。她就打电话来说,你们要不去联系器官捐献看看?
这就是“熟人社会”的效应,就像协调员为什么要去大学生中间推广,如果熟人接受了,捐献方自己的压力也会小一些,甚至还可以给对方提供帮助。比如说,当时知道这位大姐推荐的捐献者,家里有两个儿子,很内向,每天在家打游戏,职业上没有出路——高晓刚知道后,专门给他们做了一些培训,比如,怎么答辩,怎么讲话,怎么应聘,现在看两个小伙子的朋友圈,工作找到了,女朋友也有了,生活很幸福。
2021年,“协调员”这个职业有了一个变化——正式转为了红十字会志愿者,所有的协调员只能在红十字会里产生,这样一来,认可度就变化了,协调员不是劝捐,而是让相关家庭实现捐献的同时,提供养老、上学、福利待遇等一套解决方案。
目前,上海市红十字人体器官捐献服务队的协调员共有200多名,全国有3000多名。高晓刚认为,器官捐献的工作和理念,需要在象牙塔里普及。“2017年我第一次和复旦的大学生交流时,和他们探讨死亡的意义,我讲到,人这一生,应该看得远一点,就像电影《寻梦环游记》里一样,人的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