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地上的苍耳
——评耿立散文集《暗夜里的灯盏烛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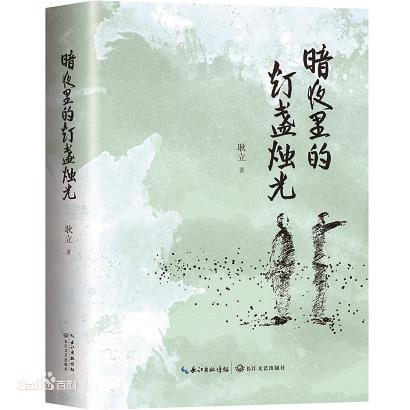
◆张林明
耿立是一腔热血之人。其散文也如梁山好汉狂饮之烈酒,但在浓烈中又不乏细腻和温柔。从北方的黄壤到南方的山海,他在南国已工作和生活多年,却依然是一颗北方大地的苍耳,倔强而执着。
《暗夜里的灯盏烛光》是耿立新出的一部散文集,由三辑二十一篇文章构成。在这些散文中,只有两篇没有出现其故乡的影子,一篇是缅怀孔夫子的《暗夜里的灯盏烛光》,另一篇是讲述了鄂伦春人与桦树的《树有其命》,剩余十九篇皆来自其“生于斯,长于斯,奔跑于斯”的鲁西南乡村大地。
耿立的文字如狂风暴雨,我被裹挟其中,不能自拔。耿立用灵动传神的文字编织了一个巨大的乡愁,网住了那些在外漂泊的游子之心。
在夜里,我抱着这本书,就像抱住了我的故乡。在耿立的笔下,这些故乡的文字们蹦蹦跳跳,来到我的跟前,幻化成故乡里的草木鸟虫和叔伯姊妹,一夜间都在我的梦里氤氲汇聚,乡音绕梁,久久不散。这是一本大地之书,这本书不仅是作者自己的文学故乡,也是那些远游者们的精神故乡。
在耿立的笔下,那一片黄壤的大地,以及大地上的万物生灵,就像从大地中走出来的,在镜头前坦陈着自己的生死爱欲,有广阔苍凉,有愁苦愤懑,有倔强不甘,有热血强悍,也有自然平和。
大地的卷轴徐徐展开,在这幅乡村画卷中——
有卑微的父亲,他形色畏缩,说话不利索。但是父爱依然如山,父亲的草帽就是遮风避雨的“乡村的屋顶”。
有教书的先生,身子瘦削,“但也觉出了骨头的硬度。”先生备受乡民尊崇,从中亦可看到乡村少年对于知识的憧憬与渴望。
有在黎明前奔跑的少年之我,少年之我在春天鲁西南平原深处的夜里奔跑,在麦子灌浆的前夜奔跑,“试图用头撞开命运的铁幕”,在奔跑中目睹了芍药花在黎明前的绽放。
有我的姐姐,“姐姐只是活着,未出嫁时,为娘家,出嫁后,为孩子。”这是那一片平原大地上的女子最常见的结局。
有血气方刚的舞龙汉子们,汉子们辗转腾挪,星星“也屏住了呼吸。”两个舞龙队,苍龙大战银龙,《十面埋伏》对《将军令》,他们在寒冬赤膊上阵,拳打脚踢,筋疲力尽,而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还有沉默的母亲,为师的二舅,木讷的表叔,父亲的酒友,唱《夜奔》的石匠师傅,打梅花拳的武师,光着膀子喝酒的徒弟们,头皮被轧花机撕掉的叫翠香的女子……
这些我们人生的过客,显影在耿立展开的乡村卷轴中,质朴自然,却又生动斐然。
人物所处之地,是铺陈的乡间风云——
有飘扬的大雪,如“深夜白色的鸦群,扇翅而至”;有萋萋芽、马蜂菜、节节草等生命力顽强的野草家族,“等春风稍微扫过地皮,那些草芽就张开口笑出声了”;有任性地在大地上奔跑的雨,给了乡村以生气,“农人就是一粒种子”,“一辈一辈地在雨水里滋养萌发”;有沉默寡言的地瓜,地瓜给了乡村以生命,父老的肤色就是地瓜的颜色。
还有那些行走在乡间的羊,在作者的笔下,生而不凡,“那弯弯的犄角,如新洗的新月,如铸铁镰刀”,“那高耸的蹄甲就是带刺的军靴”;那些好爬高的山羊,喜穿房越脊,如“乱世里的武林高手,浊世翩翩佳公子”……
耿立是多情的,也是矛盾的,他年少时想要逃离的乡村和土地,现在离得越来越远,思念却是越来越强。这些哺育了他的、年少时想要逃离的故土和故人,又何尝不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灯盏烛光呢?木镇的屋顶和屋檐将会永远是他生命的归途和灵魂的家园,那里的烛光也将永远为他点亮。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