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眼中的安特卫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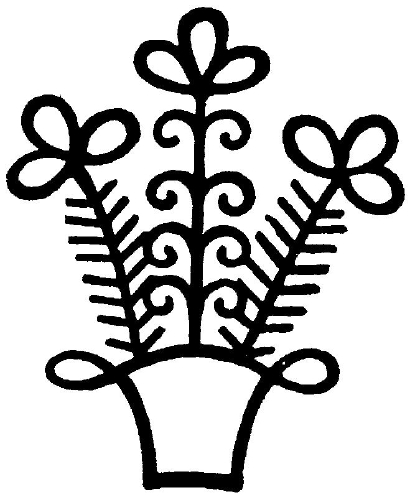
倪志琪
安特卫普这个地方常去常新。“新”可不是指城市更新的速度,欧洲这些城市大抵最难的就是改变样貌。对我来说,安特卫普是最熟悉的。
在国内参与“85美术新潮”之后,上世纪90年代初时我已经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任教六年。在那个广告摄影还不成熟的年代,视觉传达和广告招贴设计很受学设计的学生们追捧。在朋友的建议下,我来到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求学,恰逢轰动时装圈的“安特卫普六君子”毕业,整个城市充满了先锋与艺术交融的气息,直至今日,人们提起那个时候的安特卫普仍津津乐道。由教人美术转变为学习艺术,这种身份转换十分有趣。
在上海我已经在使用比利时超现实主义大师马格里特、德罗奥,立体主义大师勃拉克还有抽象主义蒙德里安德他们的绘画形式教学生画招贴画了。来到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后,学校浓烈的艺术氛围对我来说十分新鲜,各种新观念以及对新材料的运用刷新了我对于艺术表达的认知,但我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在这里,每个一心把艺术家作为职业的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创作起来似乎没有边界,但充满新的观点。而对材料的运用也大胆自由,比如有些同学会自己收集矿物,研磨后调和出属于自己的颜料;一些充满生活气息的物件也能作为作品的一部分。
尼德兰作为油画的诞生地,在留学期间,我有幸将诸多古典油画都一览无遗。以前只是听到过的鲁本斯故居、马格里特博物馆这类艺术圣地,更是吸引着我。有时,我会在下午三点去鲁本斯广场上晒太阳,坐一坐马格里特曾常坐的靠椅,试着体会下超现实主义的精神是如何偶然诞生的。同时,我也大量观看欧洲各地的当代艺术展览,经历当时的一些艺术事件,当这些优秀、充满观点的作品发生在身边的时候,我不自觉地感受到一种真实的在场感。
1995年我毕业回到上海。当时看到的艺术作品、一同讨论过的同学、吸收的新观念乃至在安特卫普的生活方式,一直影响我至今。多年之后,我再次回到安特卫普,这里的生活一切照旧,只不过我看这座城市的角度有了新的变化。中世纪就存在的咖啡厅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模样,改变的只是客人们的话题;在鲁本斯曾经喜爱的餐厅里偶然拍下宛如他画中的女性;学校附近的酒吧一直是皇家艺术学校师生的聚会场所,“六君子”也常常在此出没,交流彼此意见,如同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样。
最近一次的安特卫普之行,我动了重游那家酒吧的念头,可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我居然有点遗忘了它的具体位置。一番来回寻找之后,我发现这家中世纪古堡改造的酒吧还是没变,美院学生们仍然伴着有力的爵士乐交换想法、迸发灵感;点上一杯啤酒,也和当年一个价钱,着实有种安心的归属感。
归途中我又有了做新作品的素材。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